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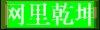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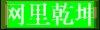 |
 |
 |
 |
·随 波·
网上聊起《洗澡》,倒让我又想起了很早以前读书时的一些感想。 曾经把《洗澡》和《围城》加以比较,隐约的看出一些有趣的对应:许彦成 之与方鸿渐,姚宓之与唐晓芙,罗厚之与赵辛楣,杜丽琳之与苏文纨/孙柔嘉, 余楠之与李梅亭之流,河马、汪?姜等于范小姐等。当然杨绛对于她笔下的人物 多少留了点情,作了一些淡化处理,不似《围城》满纸春秋,挖掘得入木三分。 网友说女主人公姚宓是一棵不动的草,我却以为她是蓄在水库里的水。表面 的沉静与老旧只是她的一层保护色,真实的她不仅聪慧有主见,且爱笑爱闹,相 当的活泼促黠--这俏皮在其与母亲“福尔摩斯”单独相处时暴露无遗,温婉之 下的傲世则惯穿她整个的言行。 姚宓的沉静,是生活使然,家庭的变故催她早早成熟,却也在成熟中消磨了 她的青春。在她把自私的未婚夫赶出生活的圈子,一个人担起家庭之担时,她就 成了一颗暗投的珠,把自己给藏了起来。灰衣底下那件锦缎绣袄便是她的象征, 只有细心人才能捕捉到偶露于布衣之外的一道锦绣的边。 许彦成捕捉到了,他的出现不经意地在水面投了一颗石子,姚宓便在层层涟 漪的推动下还原成一脉细流,叮叮咚咚跳进情感的溪流。在与许的交往中,傲世 和热情的本性一同增长,随着爱的滋生越来越显现,以至最后竟然出语要作许的 方芳,头脑热得连一向表现得玩世不恭的罗厚?(名字记不得了)都大吃一惊。 当然冷静之后,她和许还是分开了--姚和许的命运在她们刚开始时就已经 注定,曾经拥有也是姚所能获得和企求的最好结局。其中一大原因固然是杜的存 在,而姚天性之傲,所求之务完美与许之无为才是正因。这一点与围城中方唐的 分手有些异曲同工。 表面上看起来,许比方成功,且要有主见得多。事实上,他不禁没有办法摆 脱母亲的遥控,连爱情都不能自主(这一点比方还要不如),第一次婚姻是“标 准美人”玩弄他于鼓掌(此言POLITICALLY INCORRECT --更确切的说,是美人在后面推动)。而第二次如果姚宓不是积极响应和有意 的推动,许恐怕一辈子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在这一点上他是彻底地“被人牵着 鼻子走”。因此比之方唐之积极与宿命就更悲剧一些,只不过此时悲剧剧情本身 稍淡化了些。 更让人唏嘘的是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改变,姚宓仍将困在她的灰壳里,许也将 回到他的小书房和美丽默默相对终身,完成一个天成佳偶,模范夫妇的童话。而 所有的主人公内心已经不可能再回复从前的平静与无知。 另一个深爱姚宓的是罗厚,他似乎是年轻的赵辛楣。罗厚表面飞扬跳脱,可 以和导师玩笑,套学问,也可以和姚宓一起臧丕人物,漫画人生。但他并不是个 一无所知的大孩子。凭着对姚宓一点隐隐约约的爱,他最早发现姚与许之间的秘 密,劝说不成,他便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愿意当姚宓这个“方芳”的丈夫,以成 全姚许的爱和彼此的声名。如果不是有爱,哪个男子会作出这种玩笑似的选择? 同时,罗厚也是非常了解姚宓的人,他用自己的眼认识姚宓,又用世人的眼为姚 宓的处境作分析。可以说,他比许彦成更了解,甚至更爱姚宓。 罗厚和姚宓之不谐在于两者的性格。姚宓本身兼有活泼和沉静,但不知是否 出于对亡父的敬爱,她更喜欢认真深沉如父长兄一般的许彦成。罗厚只是她的一 个玩伴,一个小弟弟。而罗厚不可能也不肯为了她而改变自己的性格。当然随着 时间的更替,罗厚照旧会有新的恋爱,和许彦成赵辛楣一样重复着平淡婚姻之路。 只有姚宓此生大约会锁在一个走不出的笼子里,那张许彦成的照片将是她孤独之 旅的唯一一盏灯。 许彦成的夫人杜丽琳出身商家,大约可算是一个小家碧玉,天生了一个漂亮 的样貌,又在欧洲修过两个硕士学位,照理应当是比较的小资。比起既没有文凭, 打扮又老土的姚宓应当至少具有同等的吸引力。奇怪的是和姚宓虚无地追求爱情 相反,她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爱情,一开始追求的就是婚姻。一个稳定的家庭, 一个不沾花惹草的丈夫是她一生的终极目标。不但没有爱情,她甚至也没有一点 独立的意识。 也许是看到了乃姊的家庭悲剧,杜丽琳对自己的婚姻格外谨慎,很早就将可 靠二字作为选择丈夫的标准,并抛开一堆追求者主动追求踏实的许彦成。 这段一开始就很平淡的婚姻看起来才子佳人,配合完美得没有一点可挑剔的 地方。作为妻子,杜丽琳即使不是传统的下得厨房善于持家的贤惠,也是有一定 教养和品味的英国淑女,且“深明大义”,极善于维护丈夫的名声,可以说许杜 的婚姻主要是靠杜在维持。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姚宓和许彦成同游西山被余楠的女 儿撞见,为了维护丈夫,她硬是在还没有明白事情真相的时候就作出本能的反应, 用微笑使众人承认去西山的是她自己,撒了非常体面的一个谎。回到家,她也没 有一哭二闹三上吊,反以弱者的姿态向许表示自己的理想之消亡,最大限度是去 看看姚宓是何许人物。即使在担心可能失去丈夫的同时,她也维持了一个妻子的 立场,没有在洗澡运动中揭发出任何不利其夫的言行。而她自己,也相当成功地 通过了洗澡。 由此,换了另一个人,也许会将杜丽琳当成理想的妻子,许彦成在碰到姚宓 之前也确实没有感到什么缺憾。可是没有灵魂的美丽一旦遇上有灵性内心情感丰 富的美丽,瓷娃娃立刻就苍白无力了。美丽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她把婚姻当作人生 一场最大的交易或赌博,压上一生的平稳。她挑选丈夫,如在市集挑货,一如封 建时代的妇女,只希望终身有靠。她投资进去的也只是美丽,而不是感情。空有 一身学识,却没有独立的头脑。她所受的欧化教育除了给她一个自己挑选丈夫的 机会,对她整个世界观没有一点影响。即使明知许爱上了姚,她也不过象旧时代 的弃妇怨妇一样历数自己对家庭的贡献,以及丈夫如何的不该。至始至终,她似 乎从没有给许任何爱情(名词意义上的爱不算),也没有因许别有所爱而在感情 上重伤。事实上她似乎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怎么爱。她所做的一切努力只在尽一个 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和维持一个再也不可能完满的家。 和她相反,余楠的夫人兰英是个彻底的家庭妇女,可是这个家庭妇女有一个 相当清醒的头脑。 兰英也对爱情不抱幻想,她的丈夫不是自己所择,她也不可能与余楠大谈恋 爱,自然她的知识水平也远不如姚宓杜丽琳以及研究所的一些其他文化女性。可 她天性的纯良和生活略历的敏锐远非杜丽琳所及。 初次发现余楠在外粘花惹草之时,兰英确有一刹时的错愕与惊惶,然而她很 快就镇定下来,并立刻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设计好了一条路--这条路没有什么 特异出奇之处,却可行。一旦知道自己能独立生活不必依靠丈夫的时候,余楠在 她的生活中马上变得无足轻重,她甚至盼望着丈夫的离去,开始一个属于自己的 新生活。遗憾的是最后余楠被胡小姐抛弃了,不得不回到家中,作为妻子的兰英 只好在极度的失望中继续旧日的生活。 读到阑英,不由想起一句老话“世间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于 研究所的各色人等,兰英用自己的眼睛心灵看和品评。对余楠之鄙视使她早对婚 姻不报希望,对姚宓之关爱,是她用自己的眼看来。她也不象杜丽琳那么圆滑, 可以说出一段段美丽的谎言。她把情放在孩子身上,以致儿女稍稍伤了她的心, 她就胃病复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杜丽琳一直把自己锁在旧式的樊笼之中, 依时依势调整自己的言行。倒是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兰英保持着自己的头脑清醒 与做人的真实,并寻求独立。可惜的是无论是姚宓,还是杜丽琳,或是兰英,都 不可能走出其自身的局限。 (寄自美国)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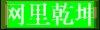 |
 |
 |
 |